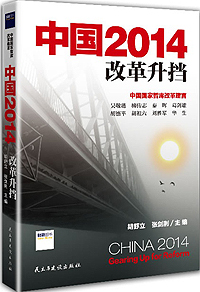 |
作者:吴敬琏 柳传志 秦晖 葛剑雄 于建嵘 胡祖六 刘胜军 华生
等
出版: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公布,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全面改革。此时此刻,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学者、企业家对土地、城镇化、都市建设、经济泡沫、垄断、税制、债务、养老、教育等当前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献言献策,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当下国人的深切关注点,体现了对改革的某种担当。就此而言,虽然这本《中国2014,改革升档》所谈大多是近年来舆论和学者反复热议的话题,但在此时重提,并将之上升至新的高度,无论你对这些专家之言有多少保留,其推动社会改革的道路坚定走下去的勇气可敬可嘉,也燃起了国人的新希望。
土地财政转型之难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金额达4.1万亿元,以超出近万亿的规模,轻松刷新了2011年3.15万亿元的历史纪录。在土地财政火爆的背后,则是各地“地王”竞相屡创新高,全国房价坐上了火箭。同时,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卖地收入作为城市基础建设重要资金来源渠道,而基础建设又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工业欠发达地区经济驱动力的重中之重,所以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实在难以整出什么像样的公共项目,就大兴楼堂馆所,甚至靠造超大规模的低智景点以吸引公众眼球。
虽然土地财政看似数目相当可观,但相较于地方动辄数千亿上万亿的空前基建规模而言,仍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迫于扩大基建数量与规模的冲动,在工商税收难以支撑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纷纷以土地作抵押,频繁举债,地方政府债务一路走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测算,“2012年,84个重点城市的土地抵押融资贷款达到5.95万亿元,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陈龙经过估测和计算后认为,截至2011年底,“中国公共债务余额为263749亿元”。
有债就必还。为平衡债务,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把目光投向土地和国有企业,但强化前者必将进一步推高“地王”高度,强化后者极易助推“国进民退”、固化垄断现象,显然与市场改革走向背道而驰。与债务混乱相伴相生的是,各级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千奇百怪,现有监管机制防不胜防,力不从心,“影子银行”也借势翻云覆雨,增加了市场的不可预测性。
再深一步追究,在土地财政背后,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经营城市思维,与之相伴的是贪大求全且高度同质化的大城市现象,“大城市病”应“运”而生。原本应以“平权”为前提的城镇化建设,在城市发展资金渴求和巨大土地利益驱动下,早就异化为土地“低进高出”的肥硕营生。就此,吴敬琏老先生从城市发展的理论高度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从‘市’也就是市场交易中心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却是从‘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当经营城市实际异化为以利益为主导,在利益先行情况下,政府的服务角色不可避免地被偷换成市场角色。实际上根本算不上市场角色,因为政府掌控资源分配大权,很难想象,政府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当土地与地方财政形成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时,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将进一步助推房价,经济的泡沫化现象也必定随之加重。
经济学者谢国忠对市场泡沫的论述看似简单但颇具智慧,“任何提议的改革举措,如果将增加债务,就应被视为支持泡沫的策略,而非改革经济的举措”。但减少债务,实际意味政府应从直接参与的市场中全身而退。
调整利益分配是最难啃的“骨头”
本书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观点,却不是一部泛泛而谈的书,各位所论敢于直视重大尖锐的时代命题,也都有各自思谋已久的解决方案,比如财政税收、城镇化建设、都市群的发展、养老等问题,所提所议所针对性极强。比如一度深陷“原罪”风波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就建议,政府在对市场环境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让政策的范围变得可以触摸,让市场中的每一个单元都局限于政策的可控范围之内,这样企业才可能集中精力向市场要效益,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寻找关系资源方面;本书还有一些文章是从宏观政策高度的睿智发声,比如吴敬琏就提出了宏观政策改革和“最小一揽子”改革计划,即“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过去支撑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要素很多,其中“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功不可没。随着改革步入深入区,原来的那些改革“红利”开发殆尽,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传统既得利益阶层。简而言之,改革就必须改变已成了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不合常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当改革矛头触碰传统利益分配机制时,必然面临如何啃下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骨头”的历史性困惑。那么,我们常说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当前社会中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国务院发展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将既得利益阶层具化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等,总人数大约8000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是,这个体量庞大的阶层几乎统揽社会优势资源分配大权,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单位的工作效率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发展的“洼地”。因此,下一步改革能否见成效,相当程度上就看触碰传统和既得利益阶层,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步子迈得有多大了。
“中国特色”原本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
如何改革这个拥有资源分配大权的庞大阶层,显然是对改革的最大考验。毫无疑问,这需要足够的智慧。即需要找准改革的切入点,从困难最小处着手,因势利导,尽最大可能降低改革阻力。智慧的凝聚本身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话语平台,一方面是因应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之需,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尽可能尊重每一个个体利益的诉求。
既是改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旦开启,可能问题庞杂,反反复复,却绝不能因此裹足不前。所以,改革需要时间,需要充分的博弈。这一过程中,可能有许多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困难和问题,如果没有非凡的意志和毅力,没有对可能的曲折的足够估计,改革非但难以达成预计效果,甚至还会导致社会负面情绪的飙升。
中国改革到了今天,笔者觉得,秦晖教授有关“中国特色”的那段话应是说最到位的:当年提出“中国特色”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指的是中国应当勇于不同于前苏联那一套,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去掉某些“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