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权力为水利工程建设和水资源的集中与分配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旦有机会,权力总会极尽可能率先“反哺”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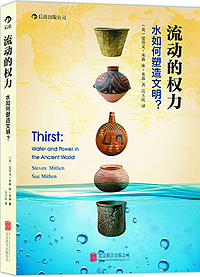 |
作者:(英)史蒂文·米森
休·米森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水孕育了人类文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所有生命均与水密切相关。可是,直到科学技术看上去已相当发达的今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却依然十分有限,至今仍旧无法完全驾驭水。对于缺乏有效工具设备特别是对自然规律还没有足够认识的古人而言,无论利用还是治理水资源,其艰难程度远非今天所能想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尚未掌握数年一遇攻关技巧的古人却给今人留下了跨越千古的文明印痕——在史蒂文笔下,无论是罗马城的地下管网,还是中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此卓然的成就,很难与权力撇清关系。
一生致力于研究水和文明的起源以及人类大脑和语言的进化的史前史考古学教授、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这部专著中,通过实地考察肥沃新月地带的费南谷地、古希腊的克诺索斯王宫、纳巴泰的卡兹涅“宝库”、古罗马的引水渠和卡拉卡拉浴场、古代中国的都江堰、吴哥王国的“内陆海洋”、美洲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等10处治水文明遗址,尝试梳理出古人如何控制、利用和争夺水资源以及水如何影响文明兴衰的历史。
催生水权力的“水壤”
从史蒂文介绍的10处文明遗址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出,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引水工程居功至伟。罗马不惜人力、财力、物力,历尽千辛万苦,建设了长达“551公里”的引水渠,其中既有穿越荒郊野外的双层渡槽,也有凿山而过的隧道。而始建于7世纪的京杭大运河更是长达1600公里。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曾详细描绘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这种集中式生产模式,既有利于均衡人力资源种植作物,显然也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公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城内修建的蓄水池和水库多达70座”,储水设施犹如一个个设计复杂且巨大的地下迷宫。
如果我们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古代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治理,本身与权力的衍生密切相关。当人类逐步告别原始游猎生活,开始过渡到定居的新生活形态时,水因素的考量就必不可缺了。出于持续获取清洁水源的初衷,人类的定居点大都会选择靠近方便取水的地方,但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定居点规模的扩大,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就一路走高。当需求超出自然界的原始供给能力时,集中与分配便不可避免。
集中与分配的首要标志,便是出现改造自然的水利设施。而水利设施的修建纵然可以依赖村落这样的自发力量,但随着人类用水和工程规模的逐步扩大,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迅速提升,权力的身影在水资源的集中与分配过程中表现得愈发突出。
如果抛开天灾以及战争等外来因素,一般情况下,水利工程越是健全的地方,其文明历史也就越为久远。建设水利工程本身是资源集中的重要体现,这种集中既体现在水源的集中调度与合理分配上,也充分体现在人力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统一调度上,甚至还包括水资源的商业开发利用。显而易见,无论哪种形式的集中与分配,都离不开权力这一坚强后盾。换言之,水资源的集中与分配需求,是催生水权力的重要“水壤”。
水权力的精英化趋势
权力介入水资源的集中与分配过程并非顺理成章。一方面,人们意识到权力在水资源的调配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权力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满足“取信于民”这一前提。在缺乏现成权力孕育架构情况下,从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管理水资源的“公信力”乃天方夜谭,或者说难以被公众接受。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困难,古人很容易便想到那些超自然力量的所谓神灵。
没有人会怀疑神灵的力量,没有人敢对神灵提出质疑。在更早的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知的局限性,虽然各种文明远隔千山万水,但从发掘的文明遗址以及流传下来的史料看,借助神灵力量以及五花八门的宗教仪式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几乎成为各个文明的共同选择。神灵力量的频频出现,显然更有助于统治人心,同时也为权力的“合法”让渡提供了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在各种文明中神灵身影无所不在。“神创造水并控制水,是苏美尔神话的主题”;“在古罗马,人们把水当成神来崇拜”;李冰父子为了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得不通过造假以便“征得”河神同意,从而达到凝聚人心目的;吴哥文明“相对于为臣民们止渴,国王们更渴望讨好印度教的神灵”……神灵本身是天赋权力的一种象征,在这种推崇神灵权力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一个关键因素,即社会精英阶层牢牢垄断了与神灵沟通的话语权,巧妙地实现了虚无神灵权力与精英阶层意愿的有机统一。
拜神灵所赐,权力的合法性终于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困难,然而权力本身又很快成为问题。水不是货币,以今天的思维,即便缺水已上升为许多国家、许多城市的重要问题,但我们还难以将水与“奢侈”两字挂起钩来。然而,史蒂文以他的考古探索告诉我们,当一种资源出现紧缺,或者权力牢牢控制资源分配大权而难受制约时,资源的功利化现象便不可避免,而功利化的背后往往又是权力的精英化。
罗马人崇拜水,对水的生活化利用走在其他文明前列,比如浴场、洗厕等等,但因大量过度使用,原本寻常的水资源逐渐沦为奢侈的盛宴。奢侈本就是社会等级化的产物,没有平民百姓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吴哥国王关心的不是灌溉与防洪,而是围绕水主题修建人间天堂。而“古典时期,作为漫长旱季至关重要而又稀缺的资源,水被玛雅精英层操纵,以此达到集中和控制权力的政治目的”……虽然权力为水利工程建设和水资源的集中与分配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旦有机会,权力总会极尽可能率先“反哺”自身。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统治者越来越意识到水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时,为达到强化统治目的,千方百计控制水资源便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理想选择。这一点,有点像我国古代的“盐经济”。食盐获取技术虽然并不复杂,但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臣民、获取税收目的,对食盐实行官办专营。自此,能从事食盐行业者,非巨商即大贾。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权力反叛者首先必须接受缺盐的困扰。虽然考古发掘结果未能证明这10处文明中有水被直接商品化的迹象,但水不仅实现了对人类基本生活的供给,同时也成为商业沟通的重要桥梁,比如“洪水迫使霍霍坎人更加密切合作”,霍霍坎人发明了通过球赛实现贸易的新路径。开掘于一千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至今在市场经济中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水孕育了文明,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权力,但水对人类的回馈不可能永无止境。在史蒂文调查的10处古文明遗迹中,“灌溉曾使苏美尔文明辉煌一时,但是在导致土壤盐碱化之后,灌溉又成为苏美尔文明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干旱居然会成为繁荣了1500年的玛雅文明迅速走向没落的导火索;在“降雨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只敬神权不顾民生的吴哥终因水利系统失灵而走向了衰败;当霍霍坎人“新的领导者曾经宣布神灵赐予他统治的权力,但是当他们抵御不了干旱和洪水时,这种权力也不复存在了”。当权力运转失灵,需要集中众多资源才能上马的水利工程几成奢望,结果霍霍坎人因无力修建水利工程不得不重回游猎的“返祖”之路……
回首人类认识水、利用水、管理水的沧桑经历,本身也是人类文明曲折发展的艰难求索。众所周知,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指乃是统治权力。其实归结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这一逻辑同样适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孕育了权力,但如果权力支配者不能做到有效保护和科学开发水资源,甚至肆意滥为、违背自然规律,那么最终大自然必定会让我们加倍偿还。从这层意义上说,史蒂文·米森所考察的10处考古遗迹,又何尝不是一个个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经典案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