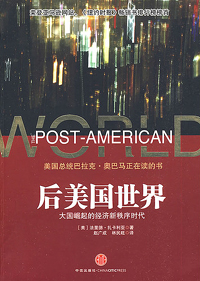 |
|
作者:(美)法里德·扎卡利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巴拉克·奥巴马一身黑色西装,头戴一副黑超特警式的太阳镜,手里拿着《后美国世界》。此时的他正在机场,行色匆匆,一边听取随行人员的汇报,一边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在了《后美国世界》中文版的封底用来宣传,上面赫然写道:“发表竞选策略,问鼎白宫,《后美国世界》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成功的法宝!也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本书。”当然,你可以完全不理会它的营销意图,因为按照常理,奥巴马读过的书何止这一本,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帮助奥巴马最终获得了“变革”的胜利还有待考究,但它至少可以作为某种隐喻,启发着我们的思考:当《后美国世界》一再追问“他者崛起的时代,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眼前这位一直倡导“我们需要改变(Change,
We need)”、“我们能够做到(We Can)”的现任总统,他又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呢?
时逢金融危机蔓延,有关世界格局演变和大国前途的话题总能引起关注,而《后美国世界》更是将议题聚焦为“美国衰落之余他者的崛起”。根据该书作者《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说法,已过去的500多年,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次权力转移都从根本上改变并塑造了世界的面貌。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第三次的权力转移,这次转移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崛起”。扎卡利亚认为,这些国家的兴起正在重塑着整个世界,经济繁荣给了它们政治自信、民族自豪、国力强大,由此必将导致旧的国际关系分崩离析、新的世界秩序重整新生。
其实扎卡利亚的观点并不新潮,类似的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露出端倪。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到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再到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他们都曾在美国霸权性力量趋于倾颓之际发出过警告——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不再下坠?如何面对其他国家的崛起?种种变化会给世界带来何种机遇和挑战?自己身处的局势有哪些问题和陷阱?未来的内政措施和外交政策又该是什么……这些命题构成了美国政治家及学者们认识美国及世界关系的基本框架及出发点,包括今天的法里德·扎卡利亚亦是如此。在书中,他尽管不无悲观地预测作为苏联解体后世界唯一超级力量的美国,现在已然不再是全世界的模范榜样,但他仍然积极地从“他者的崛起”中寻找美国重整旗鼓、再掌话语权的建国良方。
为此,法里德?扎卡利亚提出了若干原则,如“要有所选择”、“建立广泛的规则,摒弃狭隘的利益”、“成为俾斯麦,而不是学英国”、“要照单点菜,而非吃套餐”、“要善于进行非对称性思维”以及“合法性就是权力”。扎卡利亚始终承袭着“霸权护持”的观念,他建言的种种方案无不是为了美国在已是大势所趋的“后美国世界”里争取更有利的竞争态势,在扎卡利亚勾勒的世界图景里他很失望、沮丧地看到美国已唱不动“独角戏”,而是不得不参与到“小范围的大合唱”的行列之中,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保留了一丝希望和念头,就像他在书中结尾处所说的那样,“今天的美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国度:热烈欢迎来自异国他乡的每一位青年学子,就像一代人之前对待当年我这个局促不安的18岁青年那样”。不难发现,在扎卡利亚的认知里,不管“后美国世界”是如何一个走向,美国仍然很强大,区别的只有过去是“独大”,而今是“一超多强”。
扎卡利亚不是第一个也并非唯一一个提出“一超多强”的人,例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位美国当代的著名学者、“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在一次谈及“后美国时代谁来重建世界体系”时指出,“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乃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美国只是众多实力强大国家中的一员。如今我们真是身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国有八到十个,比如西欧、俄国、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实力强大;当然,美国也还是处于大国之列。经济和政治上强势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它们彼此相互竞争,同时考虑彼此之间结成不稳定的短暂联盟的可能”。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国家要在“后美国世界”中生存下来,意味着要在其所在的地区创造出相对强大的政治实体,从而使得该地区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获得统一,只有这样它才能在世界体系中占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略有不同的是,扎卡利亚认为美国仅仅处理好地区关系是不够的,它必须还得为世界提供能解决重大问题的规则、制度和服务,同时在国际体系中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留出更大的空间。不难发现,扎卡利亚有其固有的偏颇和局限,其所谓的“美国的出路”无非还是在极力鼓吹美式自由化经济、文化、政治理念的威力,甚至还露骨的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化”潮流侵蚀各国传统文化辩护,然而正是这种思维逻辑恰恰反映了美国一贯的“致命的自负”——要知道,导致中国、印度等“他者的崛起”的,却是美国所极力倡导的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使这些国家洞悉了成功的秘密所在。换言之,美国霸权的掘墓人正是美国自己。尽管扎卡利亚最终有意识到对于美国而言,“他者的崛起”不是最大的麻烦和挑战,关键的问题还是美国在应对这种冲击的过程中“自废武功”,关上了自由、开放、包容的大门,自己否定自己曾经推广的资本主义模式,但矛盾的是,他一方面希望美国继续观念领先、不闭关自守,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者的崛起”会撼动美国的地位。
事实上,从“世界是平的”对于信息技术扯平全球经济发展障碍的乐观主义,到国际关系中对于任何举动合法性要求的越来越高,到作为美国学生的发展中国家们对于美国民主及市场经济模式的学习所带给它们的良性影响,一系列因素构成了产生“后美国世界”图景的基本动力。所有的变化并非美国“一厢情愿”或者单单是“他者的崛起”就行得通的。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进步性往往就表现在,或许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永远维持它的地位永远不变。纵观往昔五百年,中国和英国就分别丧失了它们的主宰地域性或者全球性问题的话语权,今天轮到美国又何尝不可呢?对此,扎卡利亚显然是多虑了,他的“老调重弹”终究还是保守主义的翻版。